
孙隆基,历史学家。1945年生于重庆。曾在美国、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。重要著作有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、《历史学家的经线》、《未断奶的民族》、《新世界史》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: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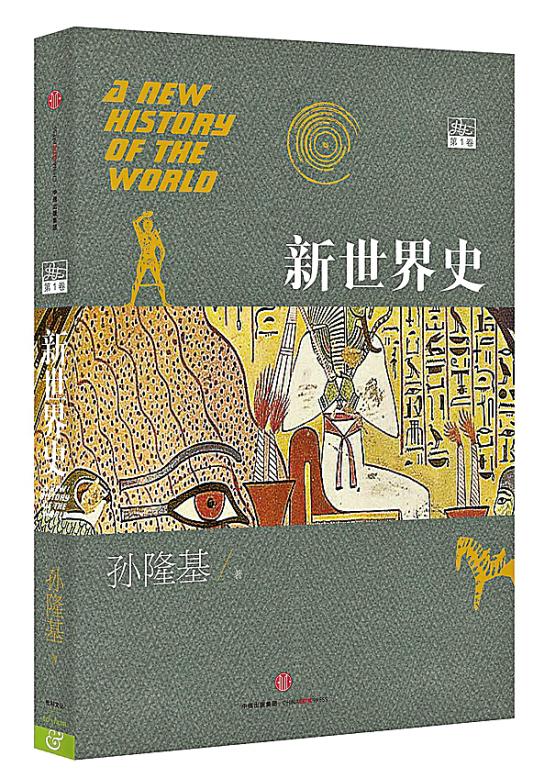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陆璐
近日,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带着他的新作《新世界史》(第一卷)来到广州与羊城读者见面。5日上午,他在华南理工大学以《中国是近代世界经济的“压仓物”?》为题做演讲;6日下午,他又以《推翻“四大文明古国”之陈说》为主题,在方所书店与广州本土学者、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对谈。
孙隆基祖籍浙江,在中国台湾及美国完成历史专业的学习和深造。1980年至1981年,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东亚史博士的他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。正是在这段时间,孙先生写出了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,1983年在香港发表,引发巨大争议。
1984年获博士学位后,孙隆基任客座教授于美国堪萨斯大学的苏联与东欧研究所与历史系,1986年获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永久教职,任职至2004年12月。2005年2月,他正式转赴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任教。十年后的今天,从他给台湾本科生上世界史的课程讲义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新作《新世界史》,与读者见面了。
“四大文明古国”通常指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印度和中国。但孙隆基认为,这是一个陈旧的概念,模糊了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。
他用农牧的辩证关系将两河文明与尼罗河文明连扣,找到其中的关键点——两者之间存在的“环阿拉伯游牧-放牧复合带”。它形成于农牧革命诞生地的环两河山侧带西段,在农牧两业中偏向“牧”;但“牧”并不是次于“农”的低级阶段,而是平行的发展。孙隆基进而认为,“游牧-放牧”并非被农耕进化抛弃后的渔猎经济的残余,而是与农耕文明平行的一种后新石器时代的形态,而“四大文明古国”则是完全从农耕文明角度看世界史的执念,他试图推翻这一陈旧的观念。
对谈
1
拿破仑如果只安心做一个小市民,他不可能成为拿破仑
羊城晚报:您在重庆出生,在香港长大,又去台湾念大学,再到美国深造攻读博士,这种经历对您的治学是否有影响?
孙隆基:我的这种经历,造成我没有归属感,但这也有好处,看问题不至于陷入某种地方、某个时代。
香港、台湾、美国,文化背景都不一样,如果一直在香港,可能我对中国文化会没有那么投入。前往台湾后,对中国史又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去到美国,那是另一种文化环境。但具体到治学,不管在哪,都有人觉得我有些大胆,但同时我会觉得是他们太胆怯,他们局限了自己的想象力,有些问题甚至连想都不去想。比如我研究心理学史的问题,评审人会觉得你居然敢写这样的题目。现在我一个人写世界史,我说自己是有“妄想症”,但这是好的“妄想症”。拿破仑如果只安心做一个小市民,他不可能成为拿破仑。
羊城晚报:您从小就对世界史感兴趣,为什么后来硕士期间念的俄国史,博士期间念的东亚史,而不是往宏观历史方向发展呢?
孙隆基:我是先对世界史感兴趣,我从在香港念中学的时候就爱看英文原版的古代希腊史,刚开始几乎每个字都要查字典,但对我的英文提高有很大帮助。去了台湾后,非要念中国史的书不可,这样才能对中国史有深入理解。在台大修俄国史是我因为听了老师讲课特别感兴趣。到了美国后,有段时间我变成了左派,对马克思主义、苏联、第三国际史很感兴趣,后来去了斯坦福就转到东亚史,因为选“俄国史”的话学校不给助学金,所以我选了东亚史。
羊城晚报:您写《新世界史》也是因为给学生上课?
孙隆基:对,最初不是我主动要写的。台湾目前的《世界通史》教科书都成于20世纪,里边还犯了很多错误,比如说匈牙利人是匈奴的后代之类。后来台大教务处委托台大出版中心找人写一部新的世界通史教科书,找到我。我在中正大学给学生上世界史的课,逐渐累积了一些讲义。教科书是入门级的世界史通识,要有基本的信息,要有死背的内容,学生考试要考。我写第一卷时还有这个味道,但写到后面发现不行,考虑改用全球史的写法,可能作重大的调整。宏观史就不是教科书了,就好像从来没有人把汤恩比的书当做教科书。
2
今天做历史学者更难了,宏观历史研究尤其有挑战
羊城晚报:所以这也是您有勇气以一己之力写世界史的原因之一?您曾谈到过,自己读书时被汤恩比的书撑得学术研究的“胃口很大”。
孙隆基:是,这和吃东西一样的。有多少人会想吃满汉全席呢?但我的看法是,不了解全盘,局部很难了解。但现在说的专业主义,都是一块块切割的,不切割不行。我认为就算是小角度的研究,也要有大历史观,否则就是瞎子摸象。
羊城晚报:为什么现在做宏观历史研究的学者比较少呢?
孙隆基:一是现在资讯爆炸,你花几辈子的功夫都没办法完全消化那些资讯,而且最新的信息还在不断地涌现出来,这也很考验功力,一些以前不注重的角落,现在都要考虑。比如我有一章是写大洋洲的,以前没有人写。今天做历史研究的困难更大了,而且很可能你的观点一出来就被否定,说你里面有些信息是过时的,对学者的挑战越来越大了。
羊城晚报:所以说其实您也有压力?
孙隆基:当然有,我需要找最新的资料,写作中要修改再修改。虽然在教学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功夫,但现在更新换代太快。我的讲义是2005年上课就开始写的,但是把全书第一卷的内容交给出版社已经是2013年。讲义变成书还是有很多空缺要补,每章还要深入研究。
3
以全球化时代的需求重绘人类的过去,最担心无人批评
羊城晚报:《新世界史》的“新”体现在哪些地方?
孙隆基:一是尽量与各历史学域最新近的进展并驾齐驱,务求胜出上个世纪甚或十年前出版的教科书。“新”的另一义是指对“全球史”这个领域的挑战,重点是去“西方中心论”——将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代的西方中心史观调整为多中心论,以今日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建构人类的“共同过去”。
全球史“全球一盘棋”的格局给新世界史提供了一个灵感,也提出一种挑战:世界史不能再以各地相互脱钩的方式编排,必须给予读者一个总图像。至目前,全球史论述仍偏重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会通的时代,如西方崛起的议题即归入此期。但“以全球化时代的需求重绘人类的过去”不能限于此,所以我这本书试图从人类文明起源阶段来实现此意图。
我现在的架构是跨地域、跨文明的,注重的是整个文明地带。比如第二卷会写贯穿欧亚洲大陆的文明链带,文明带与北方草原带有历史性互动,而欧亚大草原史也分三个时代,就是匈奴、突厥、蒙古三个霸权之间的承接。而且,我探讨了此前没有人留意过的,北方寒带林与欧亚大草原的历史生态学。这样至少减轻了旧世界史的“西方中心论”以及“农耕文明带中心论”的影响,多添了对草原带与寒带林木带的关注,才能将欧亚大陆史说得清楚。
羊城晚报:那您担心这本《新世界史》出来之后遭到其他学者的质疑或批评吗?
孙隆基:不在意的,我怕的是《新世界史》出版后,连一篇书评都没有。如果有人提意见那就很不错,我可以修改。我最担心的是连我讲错的内容都没有人指出来,连评的人都没有,就像一阵风吹过也没有吹到他们。
4
以想象力为过度实证的研究“消炎”,别鼻子贴着地面爬
羊城晚报:您的代表作《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》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,写成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了,您有没有一些观点发生了变化?
孙隆基:在这本书里,中国文化以负面的形象出现,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“现代”世局中,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。但是“现代化”本身就该不断被重新定义。萨义德《东方学》里就谈到,西方眼中的东方是他们话语里的东方,不要把它当做真正的东方。
当时我写这本书批判中国,要有个立足点,所以采取了从西方的角度来看。现在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看,中国的情形也有了变化,在这期间,我更深入地阅览了各种对中国人心理的研究,把心得加进了这本修订本中。我现在的观点没那么负面,力图避免下简单化的判断。
羊城晚报:您的历史研究观是怎样的?
孙隆基:研究历史对象并不是在心中去重演它,而是要让它更加丰富,这是一个最新的立场。至于“重演”则意味着copy,copy是不必要的,去copy的话等于没有认知者这一方,只有研究材料在独白,研究者是只有聆听的哑巴。只有你和你的研究对象两两分开这个前提下,才可能有对话。否则不是你吃掉历史,就是历史吃掉你,不可能产生对话。
我写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叙事,这个叙事是凭我的思想、智慧、功力和视野来综合决定的,这其中当然要参考其他人的著作来进行比较,但是我不会扭曲它。光实证是不够的,更主要的是洞察力。还没有人从你这个角度看过问题,这个对历史学家来说是重要的。
羊城晚报:您认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者需要具备哪些素质?
孙隆基:首先要有很严格的基础训练,对研究对象的资料要收集齐,这叫“史学”。有这个还不够,还要有“史识”,这需要一些天赋才行,否则收集齐了也就是图书馆的编目员。还需要有“史才”,有些人没有“史才”,但你问他具体的历史事件他马上能说出来,你问他某某战役的时间,能马上说出来,但你看完他的书,还是会觉得他没有把握时代或者研究对象的特点,这和天赋的能力有关系。最后,是需要想象力,它对过度实证的倾向具有“消炎”作用,不至让鼻子贴着地面爬。